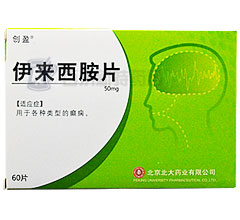您現(xiàn)在的位置: 百濟(jì)新特藥房網(wǎng)首頁(yè) >> 神經(jīng)科 >> 癲癇 >> 癲癇治療研究進(jìn)展
癲癇的藥物治療的熱點(diǎn)與爭(zhēng)論
- 來(lái)源: 百濟(jì)藥房藥訊 作者:百濟(jì)動(dòng)態(tài) 瀏覽: 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12-12-30 8:58:00
自國(guó)際抗癲癇聯(lián)盟提出重建癲癇知識(shí)新框架以來(lái),癲癇的定義、診斷方案、治療目的、腦電圖評(píng)價(jià)等都發(fā)生了根本性變化,一些癲癇診治中的深層問(wèn)題也被提出,關(guān)注癲癇診治中的問(wèn)題對(duì)于我們了解目前癲癇病學(xué)的診治變化及指導(dǎo)臨床實(shí)踐都非常重要。
一、抗癲癇藥物療效評(píng)價(jià)的多元性
在過(guò)去的20年中,人類曾先后開(kāi)發(fā)出數(shù)十種新型抗癲癇藥物,幾乎每一種新藥的臨床試驗(yàn)都能證明其有效,并得到管理部門的認(rèn)同和批準(zhǔn)。但經(jīng)過(guò)10多年的反復(fù)實(shí)踐,臨床研究人員和管理部門及從事藥物研究的學(xué)者都沮喪地發(fā)現(xiàn)癲癇藥物治療的效果并沒(méi)有比這些新藥問(wèn)世前好,癲癇有效控制率也沒(méi)有明顯上升,從而引發(fā)了研究人員的深思,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,并產(chǎn)生了新的期待。
臨床和研究人員注意到,癲癇是一種發(fā)作性疾病,用藥前后短時(shí)間內(nèi)發(fā)作次數(shù)的增減并不一定代表藥物治療的有效性。癲癇發(fā)作的無(wú)序及與某些生理周期的關(guān)系使抗癲癇藥物治療效果評(píng)價(jià)中呈現(xiàn)出其特別的安慰劑效益,即安慰劑對(duì)癲癇發(fā)作也有較高的有效率,從而使癲癇藥物治療效果的評(píng)價(jià)較其他疾病更為困難。為了克服這種療效評(píng)價(jià)的特殊性,在癲癇病學(xué)研究中常常采用多種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側(cè)面反映藥物的治療效果,如用單位時(shí)間內(nèi)發(fā)作停止率、發(fā)作減少的中位數(shù)、用藥后首次癲癇發(fā)作時(shí)間、單位時(shí)間內(nèi)未發(fā)作的天數(shù)、藥物治療的保留率等來(lái)反映藥物治療的療效,這種多元化的評(píng)價(jià)體系反映了癲癇藥物治療的特殊性,不同評(píng)價(jià)指標(biāo)反映了研究者的不同目的,因而在解讀其藥物療效時(shí)不僅要看指標(biāo),還要看其內(nèi)涵。
二、癲癇部分性發(fā)作及抗癲癇藥物選擇標(biāo)準(zhǔn)
20世紀(jì)40年代,我們沒(méi)有抗癲癇藥物的選擇標(biāo)準(zhǔn),因?yàn)槟苡糜谂R床的藥物實(shí)在太少。之后隨著國(guó)際抗癲癇聯(lián)盟癲癇發(fā)作分類的推廣和成熟,以發(fā)作類型作為抗癲癇藥物的選擇標(biāo)準(zhǔn)逐漸被人們所接受,成為傳統(tǒng)的經(jīng)典指標(biāo)。在國(guó)內(nèi)這種經(jīng)典指標(biāo)的確定可以追溯到20世紀(jì)70年代。但從那時(shí)起,癲癇病學(xué)已取得突飛猛進(jìn)的進(jìn)展,新藥不斷問(wèn)世,再加上高分辨率磁共振、功能磁共振、高分辨率腦電圖,尤其是高頻腦電圖、腦磁圖的應(yīng)用無(wú)時(shí)不在改寫(xiě)人類對(duì)癲癇疾病的了解及診治的進(jìn)步,同時(shí)也沖擊著人們現(xiàn)有的知識(shí)框架。這種數(shù)十年不變的經(jīng)典指標(biāo)已不可能反映與時(shí)俱進(jìn)的癲癇病學(xué)取得的巨大進(jìn)步,也難以得到國(guó)際組織的廣泛贊同。
癲癇發(fā)作分類的基礎(chǔ)正在發(fā)生巨大變化:⑴臨床上使用最廣泛的國(guó)際分類是1981年癲癇發(fā)作的分類,其分類的基礎(chǔ)是臨床表現(xiàn)和腦電圖。凡腦電圖表現(xiàn)為一側(cè)異常的均認(rèn)為是部分性發(fā)作,而隨著腦電圖分辨率的大幅提高,以前認(rèn)為是雙側(cè)起源的則可能由于腦電圖的高分辨率而證明其是先后而不是同時(shí)出現(xiàn)在不同腦區(qū),從而使擬診中的全面性發(fā)作成為局部起源的部分性發(fā)作;⑵癲癇臨床表現(xiàn)提示癲癇發(fā)作起源于局部者也常常被診斷為部分性癲癇,而不管其隨后是否有全身性發(fā)作。點(diǎn)燃模型是將電極置于單側(cè)動(dòng)物的杏仁核,通過(guò)反復(fù)刺激引起動(dòng)物的全身性發(fā)作,被認(rèn)為是最符合人類顳葉癲癇的模型,也是典型的部分性發(fā)作模型。隨著高分辨率磁共振的使用,許多常規(guī)影像學(xué)技術(shù)未發(fā)現(xiàn)異常的患者也可能在腦部出現(xiàn)有臨床意義的異常表現(xiàn),從而改變發(fā)作的分類,尤其是功能磁共振的日趨成熟,更加深了臨床醫(yī)生對(duì)癲癇起源的理解,從而使部分性癲癇的發(fā)作越來(lái)越多。臨床醫(yī)生也越來(lái)越相信癲癇知識(shí)的普及和技術(shù)手段的進(jìn)步正在動(dòng)搖癲癇分類的基礎(chǔ)。這帶來(lái)了2個(gè)主要問(wèn)題:①以前按全身性發(fā)作治療的部分性癲癇患者所取得的療效需要重新解釋;②隨著科學(xué)技術(shù)的進(jìn)步,更高分辨率的腦電圖、磁共振的發(fā)展還會(huì)使更多的癲癇全身性發(fā)作被分類為部分性發(fā)作,這種科學(xué)發(fā)展的趨勢(shì)使國(guó)際抗癲癇聯(lián)盟不斷修正部分性癲癇的定義。最近,國(guó)際抗癲癇聯(lián)盟提出了癲癇發(fā)作的網(wǎng)絡(luò)學(xué)說(shuō),認(rèn)為癲癇起源于單側(cè)并僅影響到網(wǎng)絡(luò)局部為部分性癲癇,影響到雙側(cè)網(wǎng)絡(luò)則為全身性發(fā)作,修改了癲癇分類的觀念。很明顯,現(xiàn)在的癲癇部分性發(fā)作與以前的部分性發(fā)作在內(nèi)涵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,因而,用以前部分性發(fā)作的概念來(lái)指導(dǎo)現(xiàn)在部分性發(fā)作患者的選藥是明顯不合適的。
抗癲癇藥物的臨床實(shí)踐也在動(dòng)搖這種依據(jù)發(fā)作類型來(lái)作為選藥標(biāo)準(zhǔn)的合理性。丙戊酸是治療全身性發(fā)作的首選藥物,但過(guò)去40多年的實(shí)踐發(fā)現(xiàn)其對(duì)部分性癲癇的發(fā)作仍然有效,且療效不低于經(jīng)典標(biāo)準(zhǔn)推薦的卡馬西平。傳統(tǒng)用于治療全身性發(fā)作的苯巴比妥、苯妥英鈉也從未被發(fā)現(xiàn)其治療部分性發(fā)作的有效性比卡馬西平差,并且由于它們價(jià)格低廉,仍在世界許多地方被廣泛使用。一些新藥,如拉莫三嗪對(duì)部分性發(fā)作的療效與卡馬西平也無(wú)明顯差異。
在癲癇病學(xué)研究中取得的進(jìn)步被大多數(shù)國(guó)際組織所接受并將這些反映在其指導(dǎo)性的文獻(xiàn)中,如美國(guó)神經(jīng)病學(xué)會(huì)在其癲癇防治指南中就將苯巴比妥、卡馬西平、苯妥英鈉、丙戊酸、奧卡西平、托吡酯、拉莫三嗪都作為部分性發(fā)作的首選藥物,英國(guó)也有類似的表述。中華醫(yī)學(xué)會(huì)臨床診治指南中也將卡馬西平、丙戊酸、奧卡西平、拉莫三嗪作為部分性發(fā)作的首選藥物而放棄了傳統(tǒng)的經(jīng)典標(biāo)準(zhǔn)。
但經(jīng)典標(biāo)準(zhǔn)中也有其合理性,這主要表現(xiàn)在失神及相關(guān)的發(fā)作方面。苯妥英鈉、卡馬西平仍然因其有加重發(fā)作的副作用而被禁用于失神發(fā)作的治療。
要走出當(dāng)前藥物治療的困境,找到合理的指導(dǎo)用藥的方法,我們需要更新觀念、獲取新思想。癲癇是一種多因素疾病,一個(gè)靶點(diǎn)的孤立選擇可能對(duì)于這種多因素疾病并不合適。大多數(shù)臨床有效的抗癲癇藥物都是通過(guò)幾種作用機(jī)制聯(lián)合起作用的(如阻斷電壓依賴性鈉或鈣離子通道,增強(qiáng)γ—氨基丁酸能的抑制,抑制谷氨酸的興奮等),同時(shí)阻斷激活典型鈉離子通道和N—甲基—D—天冬氨酸受體門控通道這兩種作用機(jī)制的聯(lián)合作用使ADCⅠ(也稱為SGB—017)在一些不同動(dòng)物癲癇模型中成為一種有效的抗癲癇藥物。除探索新的藥物指導(dǎo)原則外,我們注意到,不管是國(guó)內(nèi)或國(guó)外,多重作用機(jī)制的藥物使用越來(lái)越多,相對(duì)廣譜的抗癲癇藥物可能會(huì)越來(lái)越受到臨床醫(yī)生的青睞。
三、關(guān)于指南
抗癲癇藥物的指南是指特定情況下的藥物選擇,由于生活環(huán)境、經(jīng)濟(jì)水平、科學(xué)技術(shù)進(jìn)步程度不一致,不同國(guó)家有不同的指南。美國(guó)、英國(guó)、蘇格蘭都有自己的癲癇診治指南,國(guó)際抗癲癇聯(lián)盟也有自己的指南,這種現(xiàn)象甚至出現(xiàn)在不同的學(xué)術(shù)層面,如美國(guó)神經(jīng)病學(xué)會(huì)有神經(jīng)病學(xué)會(huì)癲癇診治指南,美國(guó)抗癲癇協(xié)會(huì)也有自己的指南,中國(guó)抗癲癇協(xié)會(huì)、中華醫(yī)學(xué)會(huì)神經(jīng)病分會(huì)、中華醫(yī)學(xué)會(huì)癲癇與腦電圖學(xué)組都有自己的指南,并不斷修改,其內(nèi)容也不盡相同,有時(shí)候還是相互矛盾的。圍繞著抗癲癇的藥物選擇,出現(xiàn)這樣多的指南,表明所反映的不是某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的自然現(xiàn)象的客觀規(guī)律,而是自然與環(huán)境、學(xué)術(shù)間相互影響的結(jié)果。與藥品說(shuō)明書(shū)、藥典、專業(yè)教材、行業(yè)規(guī)范、專家經(jīng)驗(yàn)成為藥物選擇的指標(biāo)一樣,指南也是一種供臨床醫(yī)師藥物選擇的重要指標(biāo),但不是惟一的,考慮到各國(guó)現(xiàn)有的指南都不排除醫(yī)藥公司提供的關(guān)于抗癲癇藥物研究效果的證據(jù),而令人擔(dān)憂的是許多這類的研究都是為支持市場(chǎng)戰(zhàn)略而設(shè)計(jì)的。為支持贊助者的產(chǎn)品,這些實(shí)驗(yàn)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扭曲了實(shí)驗(yàn)結(jié)果。例如,納入和排除標(biāo)準(zhǔn)的制定、對(duì)比藥物或成分的選擇、藥物滴定期、滴定率和結(jié)束點(diǎn),這些都可能影響結(jié)果,更難將指南作為一種選擇藥物的金標(biāo)準(zhǔn),管理層面和相關(guān)的法律也難以認(rèn)同。
四、抗癲癇形成與抗癲癇發(fā)作
由美國(guó)波士頓市Merritt和Putnam小組創(chuàng)始的抗癲癇藥物系統(tǒng)研究在20世紀(jì)30年代成為藥理學(xué)上的一個(gè)里程碑,其將電休克和戊士氮?jiǎng)游锬P妥鳛榭拱d癇藥物研究的經(jīng)典模型,幾乎所有的抗癲癇藥物都是通過(guò)這個(gè)系統(tǒng)篩選出來(lái)的。所研究的藥物幾乎都是作用于細(xì)胞膜,通過(guò)影響細(xì)胞上的生理通道來(lái)控制癲癇發(fā)作。由于細(xì)胞是人體的基本單位,抗癲癇藥物對(duì)其功能的影響必然會(huì)出現(xiàn)不良反應(yīng),而已知的生理通道似乎并沒(méi)有參與癲癇的形成,所以,目前的抗癲癇藥物僅有抗癲癇發(fā)作的作用,不能抗癲癇形成,更沒(méi)有明確的證據(jù)提示其能預(yù)防癲癇的發(fā)生,癲癇患者發(fā)作的消失更多的是體內(nèi)抗癲癇系統(tǒng)對(duì)疾病的修飾作用。通過(guò)揭示機(jī)制來(lái)抑制癲癇發(fā)作正成為抗癲癇形成研究的核心,一些新的藥物作用靶點(diǎn)也逐漸凸顯。(來(lái)源:王學(xué)峰 劉曉婭 《癲癇的藥物治療:值得關(guān)注的熱點(diǎn)與爭(zhēng)論》《中華神經(jīng)科雜志》 2012年4月 第45卷 第4期)
TAG:癲癇 抗癲癇藥物 癲癇病
相關(guān)藥品

神經(jīng)科導(dǎo)航
最新熱門文章
熱門藥品
- 木丹顆粒
- 腦得生膠囊
- 腦絡(luò)通膠囊
- 腦力健
- 葡立
- 礞石滾痰片
- 胡日查六味丸(水丸)
- 易倍申
- 舒血寧注射液
- 艾斯能
- 倍德林
- 芪丹通絡(luò)顆粒
- 開(kāi)浦蘭
- 悉敏
- 銀杏葉滴丸
- 利比
- 息寧
- 平康
- 兩通
- 醒腦復(fù)蘇芪龍通絡(luò)膠囊
- 欣可來(lái)
- 多功能電療綜合治療儀
- 癲癇平膠囊
- 癇愈膠囊
- 珍寶丸
神經(jīng)科藥品
便民幫助- 常見(jiàn)問(wèn)題 | 服務(wù)指南 | 藥學(xué)服務(wù) | 顧客意見(jiàn) | 顧客投訴 | 專科服務(wù) | 尋醫(yī)問(wèn)藥 | 藥師窗口
專科分類服務(wù)- 腫瘤科 | 肝病科 | 神經(jīng)科 | 精神科 | 皮膚性病科 | 眼 科 | 風(fēng)濕免疫科 | 心血管科 | 糖尿病科 | 其他科用藥
藥品導(dǎo)購(gòu)服務(wù)- 腫瘤科藥品 | 精神科藥品 | 肝病科藥品 | 眼科藥品 |皮膚性病科藥品 | 神經(jīng)科藥品 | 風(fēng)濕免疫科藥品
藥房資質(zhì)- 企業(yè)法人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 | 藥品經(jīng)營(yíng)許可證 | 藥品經(jīng)營(yíng)質(zhì)量管理規(guī)范認(rèn)證 | 食品衛(wèi)生許可證 | 互聯(lián)網(wǎng)藥品信息服務(wù)資格證